又是一年清明时。
前几天,新华社的“老小孩儿”们又一次聚会的时候,大家不禁又回忆起了4年前(2008年)在清明时节后溘然长逝的“发小”戴晓安,并相约写点追忆文章以寄托哀思。我是满口应承:应该应该,一定一定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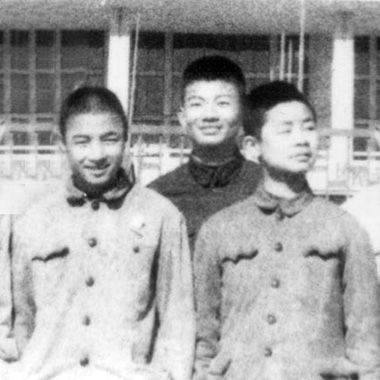
- 本文作者(左二)和戴小安(左一)
4年前在八宝山送别晓安时,我泪流满面、不能自己:实在是太突然了。谁能想到,还不到花甲之年、身体看起来很壮实的晓安,怎么说走就走了呢?走出告别室,擦干眼泪,赶往单位上班时转念一想,西哲有曰“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,而是生者的不幸”。不知道我将来有没有晓安这样的福气,走得如此潇洒。他是彻底解脱了,而我等却依旧要在乌烟瘴气的北京讨生活。
说起来,我确实最应该为晓安写点什么,我也早就想为晓安写点什么了,只是因为手懒,一直没有动笔。在半个多世纪前、20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大院里,同为小学生的晓安和我,曾是成天泡在一起、形影不离的好朋友:我们俩是同年、同学,还同住在三号楼二层西头,门对门——出了我家门,一步就能跨入晓安家——客观条件如此,想不成为好朋友都难。
1957年秋,我和晓安同时考入北京第二实验小学。那时的实验二小,虽然还不像今日侯门深似海,一票难求,但也是声名显赫,相当不容易进的了。为此,我父母提前一个星期把我从新华社皇亭子幼儿园接回了家,每天给我开“小灶”,恶补20以内的加减法之类。招生那天,父亲领着我去实验二小,恰巧在校门口遇到了幼儿园大班的小伙伴们由老师带队也来投考,让我意外惊喜。考试似乎并不难,只有口试,大都是问一些常识性的问题,父亲的精心准备全没用上。即便如此,不知何故,皇亭子幼儿园也只考上了恬恬、李周和我3人,大多数“抹泥之交”都名落孙山了。加上祖煌、晓安,新华社的孩子那一届考上实验二小的,不过5人。那时实验二小一个年级4个班,晓安在一班,恬恬、李周在三班,我和祖煌在四班。后来,丁丁、小川通过转学,也成了我们的同年同学。
记得小学开学第一天,是在八中读书的二哥启阳顺路送我去的学校。出新华社西门,沿着佟麟阁路走到手帕胡同的实验二小,大约10分钟左右。从那天放学起到小学毕业,我和祖煌等一起,在这条北京内城的老街上循环往复,一走就是6年。
晓安的父母与我的父母从延安起就是老同事,资历、职务、级别差不多,但因为只有两个孩子,生活相对宽松一点。晓安小时候身体比较瘦弱,入学后是乘坐包月的“儿童车”往返。所谓“儿童车”,不过是扣了棚的人力三轮,里面挤着五六个孩子。要放在今天,这玩意肯定是城管查抄没收的对象,但用半个多世纪前我们充满稚气的目光看去,那无异于就是今天的奔驰、宝马了。
从延安到进城后的50年代初,新华社同其他中共机关单位一样,实行供给制。那时对第二代特别照顾,有了小孩后,从柴米油盐到棉花布匹红糖鸡蛋等等什么都发,品种多数量足,孩子用不完,父母跟着沾光,以至于有“一个孩子富农、两个孩子地主”之说。不知道我的父母是不是特别想当“地主”,从延安到北京,一连生了5个孩子。结果孩子也足够多了,供给制也改为工薪制了,“地主”沦为“中农”。加上一大堆需要接济的穷亲戚,我家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。
晓安和我不仅同年,而且生日相差无几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小人书看得多了,心向往之,八九岁时的一个暑假,我俩决定效仿先贤,结为异姓兄弟,“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,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。我痴长十几二十日,便做了晓安的大哥。古人“折箭为誓”,我们没有弓箭,便找了根树枝暂代。二人相约从兹仗剑天涯,生死相助,并且相约永远保守这一秘密,不告诉第三人。今天晓安已经先我而去,我这个不称职的“兄长”,就在此将这童年的秘密公之于众吧。
那时放学回家做完作业,我经常一步跨入晓安家,一起吹牛聊天,一起看小人书,一起和晓安的哥哥小明下象棋。如果能趁小明不备,齐心协力赢他一盘,就足够我们俩高兴一天的了。我妹妹燕妮上学后,也成了晓安家的常客。也许是有4个哥哥的缘故,燕妮从小风风火火,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。她领着一帮小姑娘,和性情温和的晓安很能玩在一起,我便逐渐“退居二线”了。记得晓安的父母也很喜欢燕妮的性格,还借用民间传说中的巾帼英雄、穆桂英家中烧火丫头的名字,给她起了个绰号“杨排风”。多年后,我们都已长大成人,种地、做工,又回到北京后,晓安的父母还曾问起“杨排风”的情况。
新华社大礼堂建于民国初年,为国会开会和办公的场所。大院门外沿着内城城墙根的东西向大街,因此被命名为国会街(即现在的宣武门西大街)。清末为筹备“立宪”,清政府借宣武门内象房桥法律学堂设资政院。民国后改资政院为国会众议院,并借其东邻财商学堂作为众议院办公之地。后民国政府在财商学堂址建造了众议院部分建筑,其中包括工字楼、仁义楼、礼智楼、圆楼及国会议场等。1923年,中国现代民主史上臭名昭著的曹锟贿选,即发生于此。1949年“开国大典”前夕,新华社迁此,当时这里为北大四院所在地。新新的父亲蒋齐生、五零的父亲李慎之,都是当年提前入城挑选新社址的5人小组成员。
小时候每逢周末,大礼堂都会放映电影。一开始随便进,后来职工、家属日渐增多,便改为售票了。票价不高,五分、一角而已。于是,放电影之日,就是我们这帮男孩子的节日来临之时:虽然父母也给了钱,但我们都不买票,而是相约从三、四号楼或圆楼的暖气地下管道入口钻下去,沿着地沟爬到礼堂下面。等到灯光熄灭、电影开演的那一刻,发一声喊,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来,避开老关头等人的“追捕”,躲到礼堂某个角落里欣赏免费电影。多么紧张、多么刺激!玩得就是心跳!
其实我们最爱的“座席”,还是第一排前面、乐池周边的地上。大家挤在一起,抬头仰视近在咫尺、银光闪闪的硕大银幕,有一种十分特别的感觉。上世纪50年代的电影,以革命、战争题材为多。一到正面英雄人物壮烈牺牲或者慷慨陈词、即将英勇就义的时刻,晓安一定是紧握双拳,一边嚎啕大哭,一边用国骂帮助银幕上的英雄对抗坏蛋,任由眼泪、鼻涕在脸上冲出四条胡同,任由旁边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孩子们耻笑。
俗话说“一岁看大,三岁看老”,真是一点不错。现在都届耳顺之年了,看看周围这些老“小伙伴”,脾气秉性一如当年,丝毫未变。晓安从小就胸无城府,宽厚随和,对任何人都坦诚相见,没有丝毫戒心。也许是身体原因,他多少有点多愁善感,好动感情,很容易掉眼泪,因此有时成为一些淘气包揶揄乃至恶搞的对象,动不动就哭上一鼻子。好在晓安总是很快大雨转晴,大家又和好如初,玩在一起了。
上世纪50年代的新华社大院,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见缝插针盖满了楼,前清、民国栽种的各种树木也还没有被砍伐殆尽。这些大树可是我们童年时代最好的朋友:春天,可以爬到口子楼前的老榆树上采榆钱,回家交给妈妈蒸榆钱窝窝;夏天,小食堂南面大桑树结的累累硕果,让我们一个个吃得满嘴满牙都是紫色;秋天,西门内小院里高大挺拔的银杏满树金碧辉煌,温暖着我们的身心;冬天,大礼堂东侧的松林里,是我们堆雪人、打雪仗的最佳场所。
院里其他好玩的地方还有许多:夏天的篮球场、冬天的滑冰场,是我们驰骋嬉戏的天地,许多父母因此都给孩子买了冰鞋。跑累了,可以在松林里的石桌石凳旁小憩,这里也是我们清晨吟颂圣人文章歌赋、傍晚聚会谈天说地的好去处。在邓岗叔叔的领导下,新华社食堂主副食品花样多、味道好,在北京各大机关中声誉卓著,许多家庭都不开伙,食堂便成了孩子们聚会的又一场所。至于每年春节在这里举办的游艺晚会,更是让我们雀跃不已的欢乐时光。想看书了,高大、宽敞、肃静的图书馆里,报纸杂志乃至古今中外图书所在多有。伴我一生的阅读习惯,就是在这里养成的。记得小学二三年级时,有一次我在书库中不经意间找到了一本《呐喊》,当时还不认识“呐”字,读为“内喊”,翻开目录一看,头一篇就是《狂人日记》。“狂人还能写日记?一定很好看。”于是我用父亲的借书证将书借回家,生吞活剥、似懂非懂地看了一遍。这大概是我接受鲁迅教诲的开始。
其实从晓安和我等上小学的时候起,中国已经不复平静了:从反右派到大跃进、反右倾,从三年大饥荒到“四清”乃至“文化大革命”,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。我们的父母都曾备受煎熬甚至迫害。但是,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,这些运动带给年幼无知我们的,只有热闹和好玩。君不见,反右派、反右倾时铺天盖地、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和漫画;君不见,大炼钢铁时工字楼西窗下土高炉夜以继日的冲天火光;君不见,大跃进“放卫星”时,大院里经常举办的诗歌会上,连小脚老大娘们也组织起合唱队大唱《社会主义好》,人到中年的丁丁妈妈擦上胭脂,穿上红裤红袄,在大礼堂前跑旱船,更是轰动一时;君不见,“除四害”时全北京放假3天轰麻雀,大院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:有用气枪打的,有用二踢脚蹦的,有敲锣敲盆的,还有竹竿上绑块红布,站在楼顶上摇旗呐喊的。唉,真真是过年也没有这么令人兴奋。
当然,热闹过后三年饥荒的感觉,就不那么好受了。记得当时吃了上顿盼下顿,哪顿也吃不饱。学校中也不再大跃进,改为提倡“劳逸结合”了。最困难的时候,一天只上两节课,但无所不在的饥饿感如影随形,依然挥之不去。有一天,父亲下班时带回一块方寸大小,灰不拉几的东西,说这是新华社食堂制做的“人造肉”。当时我们已经三月不知肉味,闻之大喜,争着要吃。谁知“人造肉”入口后黏糊糊的,一股怪味,令人大失所望。
1963年上中学后,我和晓安不在同一所学校,我家又搬到了四号楼。课程渐紧,除了假期,我们见面的机会便少得多了。但只要一见面,晓安仍然是眉飞色舞,滔滔不绝,兴高采烈地说东道西。
1966年十年浩劫肇始,晓安、我及其他发小的家,几乎无一例外地被从新华社大院扫地出门。我家至少被抄了3次,搬了5次,住进了冬天滴水成冰、夏天酷热难耐的马路工棚。我们这帮孩子,也大都在经历了红卫兵造反、大串联、军训等不同阶段后上山下乡,星云流散,天各一方了。
晓安的父亲“解放”得早,因此晓安插队时间不长就参军走了。记得有一次从北大荒回京探亲时,同是休探亲假的晓安到我家来玩,让我大吃一惊:原本面黄肌瘦的晓安已经在部队锻炼成长为一个肌肉发达的棒小伙,身着国防绿的军装,更觉英气逼人。当时知青中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:“当兵是向阳花,插队是迎春花(意思是还有招工机会),兵团是苦菜花(当时兵团不允许调出,更无招工机会)。”身为“苦菜花”的我,对“向阳花”的晓安,自然是羡慕不已。
“文革”后期,“四人帮”气焰熏天,人们无不侧目而视,重足而立,三缄其口,以避飞来横祸。但老朋友不在此例,只要有见面机会,大家总是十分开心,家事国事天下事神吹海聊,交换小道消息,痛骂江青之流。关心政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特点,一个个都以天下为己任,气吞山河如虎,万户侯何足道哉!得意之际,忽忘形骸。
三十而立,这期间我们都在拼搏、奋斗,又都有了家室之累,自然不能像儿时那样整天泡在一起了,况且我还长期在外地工作。1980年代末的一个夏天,我在大连工作时,已经下海到深圳的晓安出差大连找我叙旧。当时系统内有一个几十人的专业会议正在大连召开,作为东道主,我安排与会人员到附近的一些旅游景点参观。晓安来得正好,我就一并招待了。从旅顺回来的那天晚上,会议在所住的海滨度假村会餐。给大家敬完酒后,我和晓安在一张小桌两旁对坐,就着大连的特产螃蟹、大虾,听着涛声,一边喝一边聊。“人生不相见,动如参与商;今夕复何夕,共此灯烛光?”他乡遇故知,真是人生一大快事!
1990年代中期,我终于调回北京,和晓安见面的机会反而更少了。晓安很聪明,心气很高,但这时似乎变得有点消沉,甚至连新华社老小孩们的聚会也经常缺席。不知是不是因为事业或生活中遇到点坎坷,自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?其实,老朋友就是老朋友,不会是势利眼,更不会仅仅以成败论英雄。
我在山西工作时,省上曾有一位很有魄力、很能干的领导,后来因为政坛风云变幻被请入冷宫。虽然职务、级别都没有变动,但手中的权力却几乎被清零了。因为个人关系不错,对我们单位的工作也很帮忙,在他即将退居二线时,我们一起聚了聚。酒酣耳热之际,这位老兄感慨系之地说:“现在想想,官大官小都得退,钱多钱少都是花,干好干坏都是干。”言下颇有看破红尘之意。我以为,在当今这样的大环境下,劣币驱逐良币的事情并不罕见。达则兼济天下,穷则独善其身,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总之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无论命运如何,都要豁达、乐观。
在职的时候总是穷忙,长恨此身非我有。我常常遐想,等大家都退休、有了大把富裕时间之后,诸发小们就又可以经常一起聚、一起玩,再续青少年时的友谊了。现在这一愿望基本实现,可惜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,天人相隔,与晓安只能在梦中相见了。